論商事習慣的法源位階
發布時間:2022-10-26 07:34:57
文章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網
□前沿話題□李建偉(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民法典第十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第十一條
□ 前沿話題
 (相關資料圖)
(相關資料圖)
□ 李建偉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民法典第十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第十一條規定“其他法律對民事關系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從概念法學的立場,此處需進一步作出解釋的是:“習慣”如何界定,是否包含商事習慣;“民事”如何解,民商合一體例下商事得否為特殊之民事而被“民事”包含;“商事習慣”又作何解。民法學界主流意見以為上述規定確立了“法律—習慣”二元民法淵源體系以及“商法規范—民法規范—商事習慣”三進階商法淵源體系,但也有人提出商法淵源體系應作“商法規范—商事習慣—民法規范”的解讀,分歧在于商法淵源體系下的商事習慣與民法規范之位階安排。在沒有商法典且希望“通過編纂民法典,完善我國民商事領域的基本規則,亦為商事活動提供基本遵循”的民商合一背景下,正確定位商事習慣與民法規范的位階關系,于民商事法律規范的正確適用,意義重大。
商事習慣的法源地位
商事習慣乃“商人群體集體意思自治之載體”這一立論如獲肯定,那么循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則,商事習慣在法源位階上的優先邏輯也就自洽了。在關于法律規范的諸分類中,有助于意思自治原則實現的規范類型化,乃是制定法為法定規范、習慣法為私法主體的意定規范的分類。循此,私法的法定規范之功能主要在于節省交易成本或指導交易,而不必然具有強制性,或雖具強制性,但功能僅在于建立私法自治的基礎結構,為裁判者提供裁決依據,而不在于強制影響人們的行為。“商法這個部門法更關注交易領域中建構一種最基本的秩序、誠信與安全,更強調對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設計和技術應用。”既如此,在張揚“商法的根本是意思自治精神”的商事領域,承載“商人群體的集體自治意思”的商事習慣在法源位階中的優先性的證成,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商事習慣先于民事制定法之比較法證立
創民商合一先河的《瑞士民法典》確立“制定法—習慣法—法官提出的規則”的法源位階,該法第一條所稱“本法”自然包括各編民法性質的規范,因此民事制定法優先于商事習慣。實現深度民商合一的《意大利民法典》據法典序編“一般原則”下的第一章“法源”之規定,法源包括法律、條例、行業規則和慣例等,該法第八條規定“在法律和條例調整的范圍內,慣例只有在法律和條例援引的情況下才發生效力。即使在由法律和條例援引的情況下,行業規則的效力亦優先于慣例,行業規則另有規定的除外”,也即制定法一律優先于商事習慣。意大利式民商合一體例被認為不當犧牲了商事習慣,改變了1882年《意大利商法典》第一條確立的“商事制定法—商事習慣—民法規范”法源體系。19世紀民商分立下不少商法典明確商事習慣的法源地位介于商法制定法與民法制定法之間。從解釋論出發,民事制定法與習慣法有上、下位法之分,故制定法優先于習慣法,此與采用民商分立國家不同。此處的“習慣”包括商事習慣,故商事習慣作為習慣之一自應后于民事制定法而適用,只是作為特別民事習慣優先于一般民事習慣。
商事習慣先于民事制定法的理論證成
關于習慣法與制定法的關系,民法文獻多以間接法源與直接法源、次要法源與主要法源、補充性法源與中心性法源、次要法源與本位法源、輔助法源與優先法源、非正式法源與正式法源等對應概念描述之,總的說來強調制定法處于優位、習慣法處于補充/輔助地位,可統一稱之為制定法為主、習慣法為輔的法源體系。這些概念有助于從多重視角審視兩者的關系,但并不意味著這些概念體系的正確性。這些概念體系之所以先制定法、后習慣法,邏輯依據是視習慣法為非成文法,循不成文法后于成文法適用的邏輯而成定論。實際上,所謂成文,是指對既成的規則或者做法的文字整理與記載,在此意義上,習慣可是成文的也可是不成文的,所以習慣法的對應概念是制定法而非成文法,由此可見上述概念體系之邏輯偏頗。其根本缺陷在于潛藏其后的法源觀乃是“制定法中心主義”,也即部分法律實證主義者堅持法源的制定法一元論,所謂“真正的法只是實證法,也就是特定國家的法,除此之外便沒有法”。綜上,一如法律現象、法律規范的復雜性一般,法源體系下的習慣法與制定法存在著多重的復雜關系,需要就具體私法情境而論,用任何一種此上彼下的簡單化概念描述都失之準確。在二元制的統一私法體系視野里,用多視角描述習慣法與制定法的法源位階關系,可能更臻于精確與客觀。
我國法上商事習慣法源位階的檢討與建構
但問題是,如有商事習慣與民法規定不符的,前者能否得到優先適用?質言之,如欲確立“商事制定法—商事習慣—民事制定法”位階體系,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商事習慣先于民事制定法適用的具有實益嗎?關于這一立論的證成,需要對司法實踐豐富經驗的進一步提煉與總結。例如,建材行業鋼材買賣合同中的逾期加價條款的裁判。所謂逾期加價,是指買賣合同約定買方支付的價款隨付款時間的推移而漸次增加。這一做法盛行于大宗貨物交易尤其建材市場中的鋼材買賣,長久以來習演為行業交易習慣。審理中賣方多提出逾期加價條款屬于鋼材貿易行業交易習慣、請求法院尊重并支持,但法院基本上選擇“集體沉默”,對該主張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民法典第十條“可以適用習慣”的規定束之高閣,作為法源的習慣陷入“空置化”窘境。申言之,“民商不分”本就造成了違約金規范存在“隱藏的漏洞”的客觀后果,商人們通過逾期加價條款規避違約金調減規則已屬迫不得已,漸次演變為行業交易習慣足證其存在的合理性。對此,謹慎、合理的司法應對是重要且必要的,如以商事習慣待之且先于民法上的違約金調減規則而適用,“有法誤用”的尷尬就可避免。
就民法典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的商法淵源體系及位階構成的體系解釋,民商法有不同的立場。民法學者認為,“商事法律在性質上屬于民事特別法,在商事法律沒有就相關問題作出特別規定時相關糾紛適用民事基本法的一般規則”,這一說法的背后是對“民法典+商事單行法”既有商法規范范式的堅持。但比較法研究表明,凡商法無規定的即直接適用民法的法源范式,如果說不是錯誤的也至少是不精確的。這一論爭表面上是商事習慣與民法規范之位階先后的問題,實則是對商法之于民法的實質獨立性認可度的差異。民法學者的上述立場內含了對商法獨立性的忽視,或曰對私法二元制的變相否定,由此生成了所謂民法典確立“商法規范—民法規范—商事習慣”這一商法淵源體系的解釋論。當商事制定法對某事項未有規定時,徑直向民法(典)規范尋求裁判依據,而不考慮商事習慣的法源介入,此種任意回歸民法之做法最終將損害商法之于民法的實質獨立價值。所以,確立“商事習慣先于民法規范”之位階,是保障商法之于民法的獨立性的堅實屏障,不僅可避免商事審判中法官的“任意向民法逃逸”,更可規模性地減免“有法誤用”的現象發生。因此,商法淵源體系當以恰當安排“商事習慣”的位階為要。首先,商事習慣雖與商事制定法同源,但因后者更具穩定性,商事習慣在商事制定法未規定時即可適用。其次,堅持實質私法二元制立場,商法作為私法之特別法而與民法并行存在,但基于內在體系的差異,民事制定法惟通過轉介條款方可適用于商事領域,位階上后于商事習慣。確立“商事制定法—商事習慣—民事制定法”三位階法源條款的可選立法路徑是制定商法通則,沿襲日韓商法典第一條之經驗,專設商法淵源條款。在商法通則出臺前,民法典第十條的法源條款雖一體適用于民商事,但區分民商事而各表,僅就商事場合,借助第十一條關于“特別法”(商法)規定先于民法的規定,將“特別法”解釋為包括商事制定法與商事習慣,從而確立“商事制定法—商事習慣—民事制定法”的三位階商法淵源體系。
(原文刊載于《中國法學》2022年第5期)
關鍵詞:
民商合一
樂活HOT
-
河南鞏義:1-5月累計并網分布式
一是優化工作流程,協同電力公司簡化分布式光伏項目備案、報裝等手續辦
-
股票60日均線在哪里看_股票60日
1、可在軟件上自己設置。2、60日均線是多空分界線,股價站上60日線代表
-
circle怎么讀語音 circle怎么讀
1、英[?s??kl]美[?s??rkl]圓;圓形acompletelyroundflatshapeCut
-
男子駕駛電動車不遵守信號燈,被
揚子晚報網6月14日訊(通訊員張愛國記者梅建明)6月12日上午,事故當事
-
福建省氣象局啟動重大氣象災害(
注意!今日暴雨來襲未來三天福建以陰雨天氣為主雨水上線,暫享清涼最新
-
每日熱門:格力,瞎蹭流量沒“銷
流量時代,企業爭相發力線上,變著花樣引流不足為奇。即便是老牌企業如
-
余承東回應華為 5G 芯片恢復供
愛范兒早報導讀披頭士最后一曲,AI協助完成ChatGPT推送重要更新多地高
-
聚焦:ADSCOPE:融合創新,著眼
提到工具,你想到的是什么?辦公場景中的掃描、傳輸、會議等工具,還是
-
上海:加快“元宇宙”技術體系化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近日印發《上海市“元宇宙”關鍵技術攻關行動方案
-
快報:【賽后】全員戰至終章!熱
本場賽后,巴特勒和洛瑞出席了新聞發布會。記者向巴特勒提問:在控
-
戰艦蹈浪 列陣大洋——海軍某支
作戰室內,編隊指揮員密切關注戰場態勢,指揮各艦迅速組成對空防御隊
-
商務標書包括哪些內容(五羊本田
相信大家對商務標書包括哪些內容,五羊本田哪些是獨立標?的問題都很疑
-
移動和包APP能掃微信付款,條碼
華夏時報記者付樂冉學東北京報道近日,《華夏時報》記者發現,微信支付
-
當前訊息:滬深股通|浙富控股6月
同花順數據顯示,2023年6月13日,浙富控股獲外資賣出67 14萬股,占流通
-
鄂軍贏得開門紅,13支三人女籃青
鄂軍贏得開門紅,13支三人女籃青年軍鏖戰江城---6月13日上午,“漢水杯
娛樂LOVE

安徽安慶市正式成立“老年助餐慈善基
記者日前從安慶市民政局獲悉,該市慈善會近日設立老年助餐慈善基金,共同守護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該基金專項用于資助城鄉社區老年食堂、社

安徽淮北積極落實2022年電網防汛度汛
近日,國網淮北供電公司工作人員來到110千伏中泰變電站開展防汛隱患排查。該公司積極落實2022年防汛度汛措施,提前細化應急預案,推進極端

安徽全椒縣完善拓展人力信息資源助企
今年以來,全椒縣不斷完善拓展人力資源信息庫、勞務對接信息庫、企業用工需求信息庫三庫信息資源,已摸排400多家次企業缺工崗位信息1 2萬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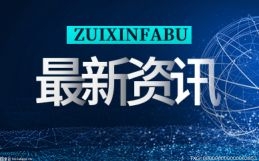
宿州市埇橋區柔性引進博士推進鄉村振
宿州市埇橋區實施博士匯工程,柔性引進29名博士擔任副鄉鎮長或園區副主任,他們將為加快產業發展、推進鄉村振興強化智力支持。目前,博士專

安徽印發出臺全面實施零基預算改革方
為進一步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益,省政府印發《安徽省全面實施零基預算改革方案》,明確從編制2023年預算起,在全省范圍內全面

5月份安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3%
近日,國家統計局安徽調查總隊發布了我省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統計數據。統計顯示,我省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 3%,同比漲幅比上月回落0 4個百分

安徽多種方式引導群眾防范非法集資風
合肥地鐵1號線、3號線上滾動播放防范非法集資宣傳視頻,淮南市發布《致老年群眾的一封信》……6月份是一年一度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宣傳月,今

鐵路部門持續加大長三角地區運力投放
記者從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有限公司獲悉,隨著上海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為進一步適應旅客出行需要,助力復工復產,鐵路部門自6月10日起持續加

安徽六安持續精準施策全力促進工業發
六安市與蔚來汽車簽署合作協議,共建智能電動汽車零部件配套產業園區。該園區一期計劃2023年上半年投產,建成后將具備年產30萬噸鋁壓鑄產能,

安徽淮北全力維護外賣送餐員合法權益
為切實防范化解新業態領域重大風險隱患,強化外賣送餐員權益保障工作,淮北市市場監管局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全力維護外賣送餐員合法權益。淮北

湖南漣源開展專項行動一對一為企業紓
位于漣源市的湖南三合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兩條生產線滿負荷運行,生產聚氨酯和巖棉復合板。因產品升級與產能擴充,急需新增兩條生產線,

湖南藍山縣進村入戶排查整治自建房安
老叔,這棟房屋墻體有開裂痕跡,要維修加固,安全重要!5月20日,藍山縣塔峰鎮果木村,黨員干部上門開展農村自建房安全隱患排查整治。連日來

一季度湖南萬元產值綜合能耗同比下降
近日,湖南省工業通信業節能監察中心發布一季度全省六大高耗能行業能源消耗統計監測報告。據該報告,一季度全省146家主要高耗能企業的萬元

濟南起步區一年來累計簽約優質項目11
萬里黃河第一隧濟南黃河濟濼路隧道建成通車,占地4000余畝的新能源乘用車零部件產業園加快施工……記者21日采訪獲悉,建設實施方案獲批復一

山東發布通知啟動傳統民居保護利用試
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省財政廳近日聯合印發《關于做好傳統民居保護利用試點工作的通知》,在全省部署開展傳統民居保護利用試點工作。此次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