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記者 孟偉
金秋時節(jié),著名公安作家呂錚又收獲了一座獎杯——第四屆茅盾新人獎。茅盾新人獎原名茅盾文學(xué)新人獎,于2014年設(shè)立,獎勵對象是45周歲以下(含45周歲)創(chuàng)作成績突出的青年作家、評論家。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此次獲獎之前,呂錚筆下的小說、報告文學(xué)、編劇作品就已經(jīng)給他帶來了諸多榮譽:《名提》獲得“首屆海峽兩岸新銳作家好書評選”十部作品之一;《三叉戟》獲得燧石文學(xué)獎懸疑類最佳長篇小說獎;《測謊師》獲得第八屆“徐遲報告文學(xué)獎”優(yōu)秀獎;編劇作品《三叉戟》獲得第27屆上海電視節(jié)白玉蘭獎最佳編劇提名、獲得第29屆華鼎獎最佳編劇提名……
近日,《法治周末》記者專訪呂錚,聽他講述連續(xù)19年筆耕不輟、佳作頻出的經(jīng)驗之談。
公安題材作品的創(chuàng)作門檻并不低
《法治周末》:對你而言,連續(xù)19年持續(xù)創(chuàng)作多部公安題材作品的動力是什么?
呂錚:主要是想告訴讀者,真正的警察是什么樣。
年輕熱血的時候,我創(chuàng)作的原動力是想把警察的故事講給別人聽。顯而易見的是:通過聊天講故事通常只有一個人聽,開座談會頂多講給100個人聽,寫成小說能有幾萬讀者,而如果拍成影視劇就能有上千萬人甚至上億人看到。
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是公安題材影視劇靠開車追逐、槍戰(zhàn)等情節(jié)就能獲得關(guān)注的時代了。隨著觀眾審美的能力和知識層次的提升,優(yōu)質(zhì)的職業(yè)劇更能吸引觀眾的眼球。對我而言,只想把最真實的故事展現(xiàn)給讀者和觀眾。
在講故事的同時,最好還能給讀者帶來些感悟。在微博上,一個女孩告訴我:“看完《三叉戟》后,我突然理解了我父親。”她的父親也是一名警察,常年無法給予家人陪伴。有一天,她突然看到父親的背影,他手里拿著泡滿枸杞的透明保溫杯。那一刻,她想起了《三叉戟》里的崔鐵軍,瞬間理解了父親工作的不易。
《法治周末》:你認(rèn)為怎樣才能寫好中國警察故事?
呂錚:許多人問我公安文學(xué)和涉案、懸疑類文學(xué)的區(qū)別。其實,很簡單的區(qū)別是:公安文學(xué)是破案的,許多涉案、懸疑是犯案的。主視角的不同,導(dǎo)致主要推動力和行動力的不同,所展現(xiàn)的人物和故事基調(diào)也會不同。
一些非公安系統(tǒng)內(nèi)的編劇創(chuàng)作的作品,用很多離奇的故事情節(jié)把警察塑造成神話。市面上,甚至出現(xiàn)了大量披著中國警服的外國警察故事。在這些公安題材影視劇中,很多情節(jié)并不接地氣。
真實的警察故事并不一定是驚心動魄的“動作戲”,而是對細(xì)節(jié)的把握、對人心的揣摩。在創(chuàng)作中,真正動人的是人的情感,一切故事都要為人服務(wù)。
所以,要想做好以破案為主基調(diào)的公安文學(xué)或者公安戲,不能生搬硬套。要避免鬧低級笑話,那就需要對基本法律常識的了解、對警隊執(zhí)法模式的掌握。再深入一點,如能寫出警察工作和生活的內(nèi)在生態(tài)等細(xì)節(jié),就更能加分了。
比如派出所的變化,現(xiàn)在派出所里有“一室兩隊”,也就是綜合指揮室、社區(qū)警務(wù)隊和執(zhí)法辦案隊。出警實行雙人工作制——每次出警都要兩個人。因此,基本不會突然出現(xiàn)孤身一人的警察穿著警服、拿槍射擊的場面。我每每在一些作品中看到這類場景,就會覺得匪夷所思。
實際上,公安題材作品的創(chuàng)作門檻并不低,并不是簡單通過采訪幾個人物就能寫好警察。
而衡量一部公安文藝作品是否優(yōu)秀,首先要看它的精神、靈魂和其中的人物,由此才能衍生出故事、情節(jié)和對白,才能展現(xiàn)出警察與警察的關(guān)系、警察與社會的關(guān)系、警察與時代的關(guān)系,才能展現(xiàn)出警察的忠誠和榮譽。
為避免“孩子變形”,走上編劇之路
《法治周末》:包括《三叉戟》在內(nèi),你已有三部作品被改編成了影視劇,還有若干部正在進行中。你如何看待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影視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guān)系?
呂錚:在《三叉戟》之前,我的兩部作品被改編成了影視劇。當(dāng)時,我自己并沒有話語權(quán),改編工作完全交給了編劇。后來,我發(fā)現(xiàn)自己辛辛苦苦寫出來的“孩子”簡直變形了,以至于我再沒向別人主動提起那些是我的作品。
編劇改編可能是迎合市場需求的,但是與當(dāng)初作品的原意常常大相徑庭。在某部作品中,我本是想展現(xiàn)兩個老無所依、為實現(xiàn)遺愿清單的男人面臨搏殺、贖罪的故事,最終卻被改編成了兄妹間相互猜疑、博弈。
當(dāng)然,電視劇是投資方、平臺、制片人、導(dǎo)演等多方集體決策的結(jié)果,很多決定需要配合或者需要說服所有人。不過,有了前車之鑒,我就一直憋著一股勁兒——到了《三叉戟》,我就要求自己要行使一部分編劇的權(quán)利。
《三叉戟》能受到觀眾的喜愛,也得益于劇中另一位編劇沈嶸。我負(fù)責(zé)“往下拽”,他來負(fù)責(zé)“飛”。好多臺詞、橋段可能太沉重的,他都能給“飛”起來。一般原著作者與編劇的合作結(jié)果都是1加1小于1,但我們倆在一起編劇能做到1加1大于1.5。這已經(jīng)算是非常成功的改編了。
《法治周末》:對于公安文學(xué)作品中的警察而言,作家如何才能讓人物鮮活起來?
呂錚:警察不是抓捕犯人的工具,他們也有自己的迷茫、痛苦和困境。公安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往往需要通過豐富人物的性格和經(jīng)歷,給觀眾呈現(xiàn)出一群有血有肉的警察。
創(chuàng)作者還要和自己對話。達到一個目的,可能有不同的寫作手法,創(chuàng)作者要思考如何讓自己的寫作手法生動且能體現(xiàn)人物性格。
在改編《三叉戟》時,我深入研究過“老三位”分崩離析的戲碼。有太多種分崩離析的可能,但怎么讓3個這么富有正義感的人有一個最合理的分崩離析的理由呢?
我最后的設(shè)計是:3個人都是對的,但是他們的層次不同,關(guān)注的重點也不同。設(shè)計這3個人的時候,我把他們當(dāng)作犬、狼、狐3種動物的化身。崔鐵軍猶如忠犬——為了忠誠可以犧牲隊友;徐國柱是“狼”式刑警,為了抓捕嫌疑人可以拿命搏;潘江海則是“狐”,有侵蝕腐敗動機的人都沖著他來,但他不僅能靈活地左右閃躲,還能將計就計、反客為主。
這樣,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理想信念,都沒有錯,但是分歧也就自然產(chǎn)生了。他們的形象已經(jīng)突破了以往對警察“偉光正”的理解,人物的塑造也都是比較立體的。同時,他們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也有一些痛苦和抉擇。
除了對人物的側(cè)寫外,外部道具的生活化也是必不可少的。
“老三位”開的那輛破金杯是有原型的。我在當(dāng)中隊長時,組里就有一輛門不好用的金杯車,新來的人只要一坐進來,我們就得提醒他把門邊的那根繩拉上,要不就容易甩出去。
公安文學(xué)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文學(xué)門類,兼具動作、對白、情節(jié)的推動。如果作者以描寫案件為主,人就容易變成一個工具。當(dāng)然,也有好多作者選擇“以人帶事”。而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探索如何兼顧這兩個方面,讓作品更豐富立體。
“我想吃糖油餅的時候,就別給我上豆包”
《法治周末》:身為公安作家,在創(chuàng)作時,你是否會有被自己的職業(yè)身份“束縛”之感?
呂錚:實際上,每部作品都會受到各方面的檢視。身上這身警服可能是約束,但是時刻提醒著我要自律。
隨著這些年受眾越來越廣,我的創(chuàng)作也越來越謹(jǐn)慎。有了影響力后,就要承擔(dān)一定的社會責(zé)任。
作者不能小覷作品的影響力。《三叉戟》播出以后,在微博上有讀者私信我,說她在大學(xué)讀的本來是非公安院校,后來因為看了我的作品,就通過公務(wù)員考試進入了公安系統(tǒng)工作。如今,她已成了我的戰(zhàn)友。
我認(rèn)為,作品首先要對得起作者自己的良心。我不建議在文學(xué)作品中肆意地將極端個例放大描寫成社會問題。一個房間的角落里有蟑螂,不代表這個房間里只有蟑螂,還可能有吊燈、壁畫、花瓶。作為作者,應(yīng)最大限度地還原這個場景,而不應(yīng)該忽視這個屋子所有的美好,只寫“蟑螂”。
在創(chuàng)作《名提》時,我有一個中心思想:搞預(yù)審的人永遠“洞悉黑暗,篤信光明”。警察每天看到各種罪惡行徑,但他們依舊會相信社會的美好,依然選擇保護善良的百姓。
《法治周末》:在法治題材的影視劇中,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情感戲?
呂錚:情感戲是一個基調(diào),但是它不能變成其中的一個要件。
拿《三叉戟》舉例,它是講三位老年警察重裝上陣的故事,觀眾選擇看就會被這三位牢牢地吸引住。哪怕情感戲?qū)懙迷倬?都不會把觀眾從戲里拽出去。情感戲的作用可以是推進劇情,或者增加人物的完整度。比如,崔鐵軍瞞著媳婦出去辦案,實際上他老婆張華是明白的。在破案回家后,張華的一句“警察真?zhèn)ゴ蟆?崔鐵軍和觀眾都能意會。張華轉(zhuǎn)身做飯時,崔鐵軍給她一個擁抱。這樣的一幕,既合理又生動。
情感戲不能為了寫而寫。我想吃糖油餅的時候,就別給我上豆包。
樂活HOT
-
股票60日均線在哪里看_股票60日
1、可在軟件上自己設(shè)置。2、60日均線是多空分界線,股價站上60日線代表
-
circle怎么讀語音 circle怎么讀
1、英[?s??kl]美[?s??rkl]圓;圓形acompletelyroundflatshapeCut
-
男子駕駛電動車不遵守信號燈,被
揚子晚報網(wǎng)6月14日訊(通訊員張愛國記者梅建明)6月12日上午,事故當(dāng)事
-
福建省氣象局啟動重大氣象災(zāi)害(
注意!今日暴雨來襲未來三天福建以陰雨天氣為主雨水上線,暫享清涼最新
-
每日熱門:格力,瞎蹭流量沒“銷
流量時代,企業(yè)爭相發(fā)力線上,變著花樣引流不足為奇。即便是老牌企業(yè)如
-
余承東回應(yīng)華為 5G 芯片恢復(fù)供
愛范兒早報導(dǎo)讀披頭士最后一曲,AI協(xié)助完成ChatGPT推送重要更新多地高
-
聚焦:ADSCOPE:融合創(chuàng)新,著眼
提到工具,你想到的是什么?辦公場景中的掃描、傳輸、會議等工具,還是
-
上海:加快“元宇宙”技術(shù)體系化
上海市科學(xué)技術(shù)委員會近日印發(fā)《上海市“元宇宙”關(guān)鍵技術(shù)攻關(guān)行動方案
-
快報:【賽后】全員戰(zhàn)至終章!熱
本場賽后,巴特勒和洛瑞出席了新聞發(fā)布會。記者向巴特勒提問:在控
-
戰(zhàn)艦蹈浪 列陣大洋——海軍某支
作戰(zhàn)室內(nèi),編隊指揮員密切關(guān)注戰(zhàn)場態(tài)勢,指揮各艦迅速組成對空防御隊
-
商務(wù)標(biāo)書包括哪些內(nèi)容(五羊本田
相信大家對商務(wù)標(biāo)書包括哪些內(nèi)容,五羊本田哪些是獨立標(biāo)?的問題都很疑
-
移動和包APP能掃微信付款,條碼
華夏時報記者付樂冉學(xué)東北京報道近日,《華夏時報》記者發(fā)現(xiàn),微信支付
-
當(dāng)前訊息:滬深股通|浙富控股6月
同花順數(shù)據(jù)顯示,2023年6月13日,浙富控股獲外資賣出67 14萬股,占流通
-
鄂軍贏得開門紅,13支三人女籃青
鄂軍贏得開門紅,13支三人女籃青年軍鏖戰(zhàn)江城---6月13日上午,“漢水杯
-
通信工程年終工作總結(jié) 今日熱搜
我從______大學(xué)光纖專業(yè)畢業(yè)后,于8月開始在縣通信分公司工作。我從事
娛樂LOVE

安徽安慶市正式成立“老年助餐慈善基
記者日前從安慶市民政局獲悉,該市慈善會近日設(shè)立老年助餐慈善基金,共同守護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該基金專項用于資助城鄉(xiāng)社區(qū)老年食堂、社

安徽淮北積極落實2022年電網(wǎng)防汛度汛
近日,國網(wǎng)淮北供電公司工作人員來到110千伏中泰變電站開展防汛隱患排查。該公司積極落實2022年防汛度汛措施,提前細(xì)化應(yīng)急預(yù)案,推進極端

安徽全椒縣完善拓展人力信息資源助企
今年以來,全椒縣不斷完善拓展人力資源信息庫、勞務(wù)對接信息庫、企業(yè)用工需求信息庫三庫信息資源,已摸排400多家次企業(yè)缺工崗位信息1 2萬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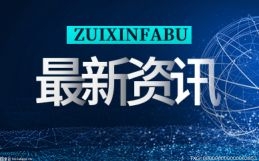
宿州市埇橋區(qū)柔性引進博士推進鄉(xiāng)村振
宿州市埇橋區(qū)實施博士匯工程,柔性引進29名博士擔(dān)任副鄉(xiāng)鎮(zhèn)長或園區(qū)副主任,他們將為加快產(chǎn)業(yè)發(fā)展、推進鄉(xiāng)村振興強化智力支持。目前,博士專

安徽印發(fā)出臺全面實施零基預(yù)算改革方
為進一步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益,省政府印發(fā)《安徽省全面實施零基預(yù)算改革方案》,明確從編制2023年預(yù)算起,在全省范圍內(nèi)全面

5月份安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3%
近日,國家統(tǒng)計局安徽調(diào)查總隊發(fā)布了我省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統(tǒng)計顯示,我省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 3%,同比漲幅比上月回落0 4個百分

安徽多種方式引導(dǎo)群眾防范非法集資風(fēng)
合肥地鐵1號線、3號線上滾動播放防范非法集資宣傳視頻,淮南市發(fā)布《致老年群眾的一封信》……6月份是一年一度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宣傳月,今

鐵路部門持續(xù)加大長三角地區(qū)運力投放
記者從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有限公司獲悉,隨著上海疫情防控形勢持續(xù)向好,為進一步適應(yīng)旅客出行需要,助力復(fù)工復(fù)產(chǎn),鐵路部門自6月10日起持續(xù)加

安徽六安持續(xù)精準(zhǔn)施策全力促進工業(yè)發(fā)
六安市與蔚來汽車簽署合作協(xié)議,共建智能電動汽車零部件配套產(chǎn)業(yè)園區(qū)。該園區(qū)一期計劃2023年上半年投產(chǎn),建成后將具備年產(chǎn)30萬噸鋁壓鑄產(chǎn)能,

安徽淮北全力維護外賣送餐員合法權(quán)益
為切實防范化解新業(yè)態(tài)領(lǐng)域重大風(fēng)險隱患,強化外賣送餐員權(quán)益保障工作,淮北市市場監(jiān)管局充分發(fā)揮職能作用,全力維護外賣送餐員合法權(quán)益。淮北

湖南漣源開展專項行動一對一為企業(yè)紓
位于漣源市的湖南三合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兩條生產(chǎn)線滿負(fù)荷運行,生產(chǎn)聚氨酯和巖棉復(fù)合板。因產(chǎn)品升級與產(chǎn)能擴充,急需新增兩條生產(chǎn)線,

湖南藍山縣進村入戶排查整治自建房安
老叔,這棟房屋墻體有開裂痕跡,要維修加固,安全重要!5月20日,藍山縣塔峰鎮(zhèn)果木村,黨員干部上門開展農(nóng)村自建房安全隱患排查整治。連日來

一季度湖南萬元產(chǎn)值綜合能耗同比下降
近日,湖南省工業(yè)通信業(yè)節(jié)能監(jiān)察中心發(fā)布一季度全省六大高耗能行業(yè)能源消耗統(tǒng)計監(jiān)測報告。據(jù)該報告,一季度全省146家主要高耗能企業(yè)的萬元

濟南起步區(qū)一年來累計簽約優(yōu)質(zhì)項目11
萬里黃河第一隧濟南黃河濟濼路隧道建成通車,占地4000余畝的新能源乘用車零部件產(chǎn)業(yè)園加快施工……記者21日采訪獲悉,建設(shè)實施方案獲批復(fù)一

山東發(fā)布通知啟動傳統(tǒng)民居保護利用試
省住房城鄉(xiāng)建設(shè)廳、省財政廳近日聯(lián)合印發(fā)《關(guān)于做好傳統(tǒng)民居保護利用試點工作的通知》,在全省部署開展傳統(tǒng)民居保護利用試點工作。此次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