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速讀:清代書商的普法力量
發布時間:2022-08-12 18:37:19
文章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廣東連山縣圣諭宣講儀式圖。■《法律與書商》作者:張婷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法律與書商》刺破了歷史的面紗,深入探究了清朝時期書商
廣東連山縣圣諭宣講儀式圖。
 【資料圖】
【資料圖】
■《法律與書商》
作者:張婷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法律與書商》刺破了歷史的面紗,深入探究了清朝時期書商是如何推動法律的普及、統治者又是如何對官吏階層和普通民眾進行法律知識教育的
□ 付杰
在不少人的認知中,我國封建王朝在法律上一直實行上智下愚的統治策略,“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封建統治者意圖使普通民眾一直處于“法盲”的狀態,自然便于統治。民間社會也有濃厚的厭訟傳統,遇有爭端,極少訴諸公堂,通常通過宗族、鄉紳等調解來定分止爭。
“舉輕以明重”,清朝作為一個滿族政權,又是封建專制皇權發展到巔峰的末代王朝,似乎更有動力實行傳統的法律策略,便于統治龐大的漢人群體。
真實情況是否如此呢?張婷教授的《法律與書商:商業出版與清代法律知識的傳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一次系統而深入的祛魅。原來,在樸素的認知之外,歷史深處還有很多有待挖掘的事實與細節。正是在這種學術挖掘活動中,歷史才得以呈現出它更為生動真實的面貌。
《法律與書商》融合了清朝的法律史和出版史,作者在閱讀眾多文獻的基礎上,旁征博引,嚴格論證,深入考察了清朝法律圖書的商業出版、統治者的法律教育與宣傳策略以及普通百姓的法律意識等問題,進而得出了許多不同以往的新穎觀點,也厘清了我們關于清朝法律教育與民眾法律意識的幾個迷思。
法律圖書的商業出版
中國法律史課程中的清朝部分,通常只講述《大清律例》《大清會典》、欽定各部則例等官方的成文法律,對于民間社會是否可以印刷、傳播這些成文法律則付之闕如,《法律與書商》對民間如何出版法律圖書進行了詳盡描述。
武英殿是清朝的官方出版機構,負責刊刻朝廷出版發行的儒學、史學、醫學等百家書籍,從1725年“雍正律”開始,又負責刊刻所有的欽定版清律。但武英殿是官辦機構,不面向市場需求,不追求經濟效益,因此圖書刊刻效率低下,無法滿足民間對律典的需求,這就為商業出版的出現提供了機會。
有清一朝,除了雍正帝和乾隆帝時代曾頒發過對法律書籍出版的嚴格管控政策,其他時期對法律出版物均實行較為寬松的規制措施,清早期甚至對此不加干預,法律書籍的商業出版也就有了足夠的生存空間。
清早期和晚期的法律出版物要多于清中期,尤其是晚清時期,多個版本互相競爭,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些民間出版的官方法律被簡稱為坊刻版。
相比于內容固定、形式單一的殿版律典,坊刻版要吸引讀者購買,回應市場需求,因此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做了重大改進,除了刊刻律典原文外,還添加了詳細的律例注解、各部則例、判例、交叉索引等豐富的法律知識,并且通常有清晰明了的總索引,便于檢索相關法律,因而更受社會歡迎,也更易購得,其受眾群體不僅包括普通文人,還包括官員、幕友等體制或半體制人士。
可以說,坊刻版律典的商業出版與發行是一場針對官方壟斷法律的去中心化運動,深刻形塑了清朝的法律教育與司法實踐。
針對官員的法律培訓
人們通常會認為,清朝的官員極少具備完善的法律知識,因此需要仰仗幕友協助鞫讞之事,以至于形成了“紹興師爺”這一龐大的職業群體。但張婷教授通過研究發現,清朝政府十分重視朝廷官員的法律知識和實踐技能,并形成了系統的法律培訓制度和法律研習慣例。
清朝律典明文規定官員應掌握法律知識,“凡國家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在外各從上司官學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官罰俸一月,吏笞四十”。此外,還在詔令和規章中強調了對官員法律知識的考察,如刑部1725年宣布,所有低階司官每年年底必須參加一次考試,背誦律典中的規定,考試成績關系到晉升與否。
為了解決積壓案件,提高司法運作效率,刑部在1860年又規定所有到部新任司官要跟現任司官學習兩年法律理論與司法實踐,完成后方能獨自辦案。為了進一步規范官員法律培訓制度,清朝還于1866年出臺法令,推出新的法律考試形式,要求官員必須熟習法律,否則將影響晉升錄用
在官員的法律培訓上,清朝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審局制度。發審局負責處理京控交審案件、提省后發交案件、刑部駁回案件等,在省級司法運行系統中有重要作用,因此也就成了缺乏經驗的官員觀摩與研習法律的理想場所。多省都要求新任官員和候補官員須在發審局接受一年的法律培訓,被評估合格后方可錄用或晉升。
除了朝廷制定規章制度培養官員的法律技能外,很多官員出于仕途之需,也自覺學習法律,提升法律素養。張婷教授的研究表明,無論是官員閱讀的書目,還是收藏的書籍,在四書五經、詩詞文章之外,都有實用取向的法律書籍。由于坊刻版律典的興盛,官員也易于買到此類書籍,這就為他們學習法律提供了便利。
廣為流通的訟師秘本
《論語·顏淵篇》有句十分有名的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儒家追求“無訟”的倫理觀念深刻影響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法律策略,從而在民間社會中形成了十分強烈的厭訟、賤訟、恥訟情緒。但張婷教授通過研究《淡新檔案》《清稗類鈔》等文獻,發現民眾在厭訟的另一面,還有一些人具有強烈的法律意識,甚至利用和操縱法律來達到自己的非法目的。那么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了解法律知識的呢?
如上文所述,坊刻版律典雖然在市面上流通甚廣,但對于底層百姓來講,不僅價格比較昂貴,而且難以理解。他們學習法律的渠道,主要是通過低廉通俗的訟師秘本。
訟師秘本是近代中國通俗法律文學中的重要文類之一,也可以理解為通俗法律讀本,主要是通過精簡生動的案例、朗朗上口的歌訣、簡潔明了的問答等形式傳授法律知識。清朝比較流行的訟師秘本有《驚天雷》《法家新書》《刑臺秦鏡》等。盡管內容簡略、紙張粗糙,甚至內容也多有疏誤,但由于精準拿捏了底層百姓法律需求的“痛點”,因而極受民間社會的歡迎。
不同于坊刻版律典,由于訟師秘本鼓吹訴訟,在朝廷看來無異于傳播有害知識,擾亂社會秩序。盡管被嚴格限制在市場上流通,訟師秘本依然廣泛傳播。普通百姓正是通過這種渠道了解了許多有關婚姻、繼承、買賣、盜竊、謀殺等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知識,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他們樸素的法律意識,進而影響了他們的法律行為。
民間社會的法律教育
清朝并非如我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封建統治者壟斷了法律的制定權和解釋權,使民眾對法律處于一種茫然無知的蒙昧狀態。研究發現,清朝除了對官吏制定了法律培訓制度,在民間社會也推行了通俗法律教育制度。當然,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并非為了啟發民智,促進民權,而是明示法律的嚴酷性以威懾犯罪行為,維護統治穩定,同時發揮法律的道德教化作用,改善社會風俗習慣。
在諸多法律教育渠道中,最為重要的是圣諭宣講制度。需要說明的是,這一制度并非清朝首創,自宋至明都有此實踐。圣諭宣講的內容不僅包括儒家傳統道德,還包括律典條文;宣講形式則是借助民間鄉約組織進行,到了明清時期,鄉約組織的核心特征由“自愿加入、鄉紳主導、地方自治組織轉為強制參加、官員主導、國家支持的宣講儀式”。
清代的圣諭宣講更是包括大量的法律知識,這在圣諭宣講手冊中可見一斑,如最有影響力的《上諭合律鄉約全書》《圣諭十六條附律易解》,均包括大量有關戶律、刑律的律例原文,并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加以解釋。通過圣諭宣講這種大型普法形式,大量不識字、不懂法的普通百姓能夠了解到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法律知識,接受了最為基礎的通俗法律教育。
《法律與書商》刺破了歷史的面紗,深入探究了清朝時期書商是如何推動法律的普及、統治者又是如何對官吏階層和普通民眾進行法律知識教育的。這本書也打破了我們腦海中的思維定式,有助于我們了解法律在清朝社會的具體運作機制,以及統治者、民眾與法律之間的互動關系。也許書中的研究未必全然準確,但它提供了一塊拼圖,通過作者嚴謹的學術研究和求真的學術精神,拼湊出了更為完整的歷史譜系,也揭開了更為真實的歷史面貌。
樂活HOT
-
股票60日均線在哪里看_股票60日
1、可在軟件上自己設置。2、60日均線是多空分界線,股價站上60日線代表
-
circle怎么讀語音 circle怎么讀
1、英[?s??kl]美[?s??rkl]圓;圓形acompletelyroundflatshapeCut
-
男子駕駛電動車不遵守信號燈,被
揚子晚報網6月14日訊(通訊員張愛國記者梅建明)6月12日上午,事故當事
-
福建省氣象局啟動重大氣象災害(
注意!今日暴雨來襲未來三天福建以陰雨天氣為主雨水上線,暫享清涼最新
-
每日熱門:格力,瞎蹭流量沒“銷
流量時代,企業爭相發力線上,變著花樣引流不足為奇。即便是老牌企業如
-
余承東回應華為 5G 芯片恢復供
愛范兒早報導讀披頭士最后一曲,AI協助完成ChatGPT推送重要更新多地高
-
聚焦:ADSCOPE:融合創新,著眼
提到工具,你想到的是什么?辦公場景中的掃描、傳輸、會議等工具,還是
-
上海:加快“元宇宙”技術體系化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近日印發《上海市“元宇宙”關鍵技術攻關行動方案
-
快報:【賽后】全員戰至終章!熱
本場賽后,巴特勒和洛瑞出席了新聞發布會。記者向巴特勒提問:在控
-
戰艦蹈浪 列陣大洋——海軍某支
作戰室內,編隊指揮員密切關注戰場態勢,指揮各艦迅速組成對空防御隊
-
商務標書包括哪些內容(五羊本田
相信大家對商務標書包括哪些內容,五羊本田哪些是獨立標?的問題都很疑
-
移動和包APP能掃微信付款,條碼
華夏時報記者付樂冉學東北京報道近日,《華夏時報》記者發現,微信支付
-
當前訊息:滬深股通|浙富控股6月
同花順數據顯示,2023年6月13日,浙富控股獲外資賣出67 14萬股,占流通
-
鄂軍贏得開門紅,13支三人女籃青
鄂軍贏得開門紅,13支三人女籃青年軍鏖戰江城---6月13日上午,“漢水杯
-
通信工程年終工作總結 今日熱搜
我從______大學光纖專業畢業后,于8月開始在縣通信分公司工作。我從事
娛樂LOVE

安徽安慶市正式成立“老年助餐慈善基
記者日前從安慶市民政局獲悉,該市慈善會近日設立老年助餐慈善基金,共同守護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該基金專項用于資助城鄉社區老年食堂、社

安徽淮北積極落實2022年電網防汛度汛
近日,國網淮北供電公司工作人員來到110千伏中泰變電站開展防汛隱患排查。該公司積極落實2022年防汛度汛措施,提前細化應急預案,推進極端

安徽全椒縣完善拓展人力信息資源助企
今年以來,全椒縣不斷完善拓展人力資源信息庫、勞務對接信息庫、企業用工需求信息庫三庫信息資源,已摸排400多家次企業缺工崗位信息1 2萬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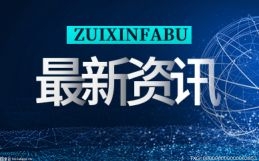
宿州市埇橋區柔性引進博士推進鄉村振
宿州市埇橋區實施博士匯工程,柔性引進29名博士擔任副鄉鎮長或園區副主任,他們將為加快產業發展、推進鄉村振興強化智力支持。目前,博士專

安徽印發出臺全面實施零基預算改革方
為進一步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益,省政府印發《安徽省全面實施零基預算改革方案》,明確從編制2023年預算起,在全省范圍內全面

5月份安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3%
近日,國家統計局安徽調查總隊發布了我省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統計數據。統計顯示,我省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 3%,同比漲幅比上月回落0 4個百分

安徽多種方式引導群眾防范非法集資風
合肥地鐵1號線、3號線上滾動播放防范非法集資宣傳視頻,淮南市發布《致老年群眾的一封信》……6月份是一年一度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宣傳月,今

鐵路部門持續加大長三角地區運力投放
記者從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有限公司獲悉,隨著上海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為進一步適應旅客出行需要,助力復工復產,鐵路部門自6月10日起持續加

安徽六安持續精準施策全力促進工業發
六安市與蔚來汽車簽署合作協議,共建智能電動汽車零部件配套產業園區。該園區一期計劃2023年上半年投產,建成后將具備年產30萬噸鋁壓鑄產能,

安徽淮北全力維護外賣送餐員合法權益
為切實防范化解新業態領域重大風險隱患,強化外賣送餐員權益保障工作,淮北市市場監管局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全力維護外賣送餐員合法權益。淮北

湖南漣源開展專項行動一對一為企業紓
位于漣源市的湖南三合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兩條生產線滿負荷運行,生產聚氨酯和巖棉復合板。因產品升級與產能擴充,急需新增兩條生產線,

湖南藍山縣進村入戶排查整治自建房安
老叔,這棟房屋墻體有開裂痕跡,要維修加固,安全重要!5月20日,藍山縣塔峰鎮果木村,黨員干部上門開展農村自建房安全隱患排查整治。連日來

一季度湖南萬元產值綜合能耗同比下降
近日,湖南省工業通信業節能監察中心發布一季度全省六大高耗能行業能源消耗統計監測報告。據該報告,一季度全省146家主要高耗能企業的萬元

濟南起步區一年來累計簽約優質項目11
萬里黃河第一隧濟南黃河濟濼路隧道建成通車,占地4000余畝的新能源乘用車零部件產業園加快施工……記者21日采訪獲悉,建設實施方案獲批復一

山東發布通知啟動傳統民居保護利用試
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省財政廳近日聯合印發《關于做好傳統民居保護利用試點工作的通知》,在全省部署開展傳統民居保護利用試點工作。此次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