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速遞!一部“有趣有益有料”的法學研究筆記
發布時間:2022-07-29 15:22:57
文章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通過一篇篇短小精悍、文筆洗煉、圖文并茂的文章,作者講述了自己是如何開啟“法律與社會科學”研究之門,在何時何地撞了墻、摔了跤,又是如何“柳
通過一篇篇短小精悍、文筆洗煉、圖文并茂的文章,作者講述了自己是如何開啟“法律與社會科學”研究之門,在何時何地撞了墻、摔了跤,又是如何“柳暗花明”的;學術道路上獲得了哪些人和作品的幫助、激勵,對法律獲得了哪些洞見;是如何不懈地進行學術寫作,又是如何攻克“發表”這一“生死”難關的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 任岳鵬
《街頭的研究者:法律與社會科學筆記》(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是賀欣教授所著的一部“有趣有益有料”的作品。
本書在行文中沒有采用“社會法學”而是采用了“法律與社會科學”這樣的表述。
在筆者看來,要理解本書的內容、特色和貢獻,有必要先了解何謂社會法學,而這就必須聯系三大法學流派也即法的三大研究視角、方法來談。
三大法學流派
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受社會因素影響,其認識和研究視角、路徑必然是多元的。總體上說,人們對法律有3種不同的認識,也可說有3種不同意義上的法律,即3種法律觀。
其一,認為法律是人類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體現著人類社會公認的普適價值。其二,認為法律是國家創立的法律規范,是一種事實上的國家規定或者說規范事實。其三,認為法律是現實社會中人們實際遵循即實際有效的行為規則,是一種社會事實。
由于人們對法律有這樣3種根本不同的認識,在法律思想史上也就形成了三大法學理論、流派。即,自然法學(主張法即體現普適價值的自然法)、分析實證法學(簡稱分析法學,主張法即實在法)和社會法學(主張法即社會中實際有效的規則,也即行動中的法)。
法律觀和方法論是統一的,三大法學理論也就是三大法學研究方法。即從普適價值角度研究法律的自然法學的價值分析方法、從實在法本身研究法律的分析法學的規范分析方法、從社會現實視角研究法律的社會法學的社會實證方法。
就法的三大研究視角、方法的關系來看,從發生學上講,可以說,自然法學最古老,分析法學最正宗,社會法學最現實。
自然法學產生于古希臘、經過起起伏伏一直延續發展到今天。分析法學產生于19世紀上半葉,其立意就在于強調法學的獨立性和科學性,力求把法學與探討正義問題的哲學、倫理學區別開來。社會法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隨著社會學的產生,以及回應西方社會嚴峻的社會矛盾和復雜多變的社會現實而出現的。
從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來分類的話,分析法學屬于法的內部研究視角,自然法學和社會法學則屬于法的外部研究視角。從價值研究和實證研究來分類的話,自然法學屬于價值研究,分析法學和社會法學則屬于實證研究。
當然,由于人們認識的固有局限性,三大法學理論也是各執一詞,互相批判。自然法學強調法律的價值和目的,但往往被譏諷為“空洞、胡說”。分析法學強調了法律自身的獨立性、體系性、安定性,但往往被批評為“機械、教條”。社會法學強調要關注復雜多變生動的社會現實,但往往因為流于現象描述而讓人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感。
學術研究心路
近些年,中國學界出現的“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之爭,實質上就是分析法學研究范式與社會法學研究范式之爭。當然,對于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提出的“社科法學”這一概念,學界有不同觀點。有的主張應仍然使用“社會法學”這個稱謂,有的主張應使用“法律與社會科學”這種表述方式。賀欣教授的這部著作就是采用了“法律與社會科學”表述。
不過,不管使用哪種表述和稱謂,其意指的研究視角和研究對象是一樣的。即研究社會現實中的法律現象,重在說明法律與社會的相互影響、相互關系。如果非要指出社會法學與“法律與社會科學”的區別的話,正如賀欣教授在書的開篇所指出的,“法律與社會科學”泛指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包括人類學、語言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等)而不僅是社會學的方法,從外部視角研究法律現象。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當今中國仍處于社會現代化轉型期,社會復雜多變是不爭的現實。因而,強調從社會現實出發,運用當代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認識、研究法律現象,就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那么,從“法律與社會科學”本身出發,賀欣教授的這部著作又有什么特色和貢獻呢?
首先,書名中的“筆記”兩個字告訴我們,這不是一部用社會學方法進行研究而得出的學術成果,而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科學”的心得體會。進而,“街頭的研究者”主標題告訴我們,這也不是一部生硬地教導我們如何進行“法律與社會科學”研究的著作,而是作者以“街頭的研究者”身份自居、對自己學術研究之路的回顧和分享。
本書通過一篇篇短小精悍、文筆洗煉、圖文并茂的文章,融學術性、思想性與故事性于一體。作者講述了自己是如何開啟“法律與社會科學”研究之門的,又是如何“登堂入室”的;在何時何地撞了墻、摔了跤,又是如何“柳暗花明”的;學術道路上獲得了哪些人和作品的幫助、激勵,對法律獲得了哪些洞見;是如何不懈地進行學術寫作,又是如何攻克“發表”這一“生死”難關的。
“法言法語”之外
書中閃光之處俯拾皆是,但掩卷后尤其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有3處:關于斗雞的故事、關于法律話語的探討、關于論文特別是英文論文寫作與發表的經驗分享。
書中通過講述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關于巴厘島斗雞活動的研究等告訴我們,當警察到來時,和當地民眾一起逃跑,能獲得對田野調查來說非常關鍵的第一步——“身份認同”;而且,警察不僅是正式制度即法律的執行者,也是非正式制度的參與者——正是由于他們的執法方式,人們才會放心地進行斗雞活動。
根據福柯的思想,話語是一種權力即話語權,這一點在今天已經成為共識。本書中,作者進一步介紹了美國學者薩里·梅麗(Sally Merry)的研究發現,即法庭上法官和律師不僅要運用法律話語,還要運用道德話語(即指出道德的要求)和療傷話語(即通過安慰、說服的方式撫慰對方的傷痕)。
這一點突破了我們一直以來強調的法律人應運用“法言法語”的片面認識。換句話說,基層法官和法律工作人員要能勝任工作、把工作做好,就必須根據情況運用上述3種話語,而不是只會運用法律專業術語和當事人打交道。
對于學術作品發表,作者一句“不發表,等于零”無異于“當頭棒喝”,驚醒了我等在學術道路上蹣跚、迷茫之輩。屢敗屢戰,要的不僅是勇氣,還有如同球場上的戰術、技巧。而作者從一個高中、大學里的英文差等生,竟然蛻變成一個英文學術寫作的高手,這一劍是如何在十年內磨出來的?作者的經歷和經驗分享,對于母語非英語而又有英文學術寫作欲求的我們來說,無疑具有極強的參考價值和激勵作用。
我們傳統文化對教師和文人的要求,有“身教重于言教”“立言立德”之說。在筆者看來,本書內容實現了身教與言教的融合,作者不僅在講解“應該如何”,而且在解剖“我是如何”。從字里行間,從作者分享的一則則親身經歷,我們能夠觸摸到一個“真誠、獨立、有趣”的靈魂。
本書特別在書末“緬懷梅麗老師(代后記)”,讀后令人感懷不已。梅麗并非是作者的正式導師,但又是他真正的學術導師。在這種學術緣份中,我們不僅了解了梅麗老師的貢獻,也了解了作者的為人。
(作者系天津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樂活HOT
-
股票60日均線在哪里看_股票60日
1、可在軟件上自己設置。2、60日均線是多空分界線,股價站上60日線代表
-
circle怎么讀語音 circle怎么讀
1、英[?s??kl]美[?s??rkl]圓;圓形acompletelyroundflatshapeCut
-
男子駕駛電動車不遵守信號燈,被
揚子晚報網6月14日訊(通訊員張愛國記者梅建明)6月12日上午,事故當事
-
福建省氣象局啟動重大氣象災害(
注意!今日暴雨來襲未來三天福建以陰雨天氣為主雨水上線,暫享清涼最新
-
每日熱門:格力,瞎蹭流量沒“銷
流量時代,企業爭相發力線上,變著花樣引流不足為奇。即便是老牌企業如
-
余承東回應華為 5G 芯片恢復供
愛范兒早報導讀披頭士最后一曲,AI協助完成ChatGPT推送重要更新多地高
-
聚焦:ADSCOPE:融合創新,著眼
提到工具,你想到的是什么?辦公場景中的掃描、傳輸、會議等工具,還是
-
上海:加快“元宇宙”技術體系化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近日印發《上海市“元宇宙”關鍵技術攻關行動方案
-
快報:【賽后】全員戰至終章!熱
本場賽后,巴特勒和洛瑞出席了新聞發布會。記者向巴特勒提問:在控
-
戰艦蹈浪 列陣大洋——海軍某支
作戰室內,編隊指揮員密切關注戰場態勢,指揮各艦迅速組成對空防御隊
-
商務標書包括哪些內容(五羊本田
相信大家對商務標書包括哪些內容,五羊本田哪些是獨立標?的問題都很疑
-
移動和包APP能掃微信付款,條碼
華夏時報記者付樂冉學東北京報道近日,《華夏時報》記者發現,微信支付
-
當前訊息:滬深股通|浙富控股6月
同花順數據顯示,2023年6月13日,浙富控股獲外資賣出67 14萬股,占流通
-
鄂軍贏得開門紅,13支三人女籃青
鄂軍贏得開門紅,13支三人女籃青年軍鏖戰江城---6月13日上午,“漢水杯
-
通信工程年終工作總結 今日熱搜
我從______大學光纖專業畢業后,于8月開始在縣通信分公司工作。我從事
娛樂LOVE

安徽安慶市正式成立“老年助餐慈善基
記者日前從安慶市民政局獲悉,該市慈善會近日設立老年助餐慈善基金,共同守護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該基金專項用于資助城鄉社區老年食堂、社

安徽淮北積極落實2022年電網防汛度汛
近日,國網淮北供電公司工作人員來到110千伏中泰變電站開展防汛隱患排查。該公司積極落實2022年防汛度汛措施,提前細化應急預案,推進極端

安徽全椒縣完善拓展人力信息資源助企
今年以來,全椒縣不斷完善拓展人力資源信息庫、勞務對接信息庫、企業用工需求信息庫三庫信息資源,已摸排400多家次企業缺工崗位信息1 2萬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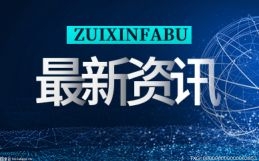
宿州市埇橋區柔性引進博士推進鄉村振
宿州市埇橋區實施博士匯工程,柔性引進29名博士擔任副鄉鎮長或園區副主任,他們將為加快產業發展、推進鄉村振興強化智力支持。目前,博士專

安徽印發出臺全面實施零基預算改革方
為進一步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益,省政府印發《安徽省全面實施零基預算改革方案》,明確從編制2023年預算起,在全省范圍內全面

5月份安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3%
近日,國家統計局安徽調查總隊發布了我省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統計數據。統計顯示,我省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 3%,同比漲幅比上月回落0 4個百分

安徽多種方式引導群眾防范非法集資風
合肥地鐵1號線、3號線上滾動播放防范非法集資宣傳視頻,淮南市發布《致老年群眾的一封信》……6月份是一年一度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宣傳月,今

鐵路部門持續加大長三角地區運力投放
記者從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有限公司獲悉,隨著上海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為進一步適應旅客出行需要,助力復工復產,鐵路部門自6月10日起持續加

安徽六安持續精準施策全力促進工業發
六安市與蔚來汽車簽署合作協議,共建智能電動汽車零部件配套產業園區。該園區一期計劃2023年上半年投產,建成后將具備年產30萬噸鋁壓鑄產能,

安徽淮北全力維護外賣送餐員合法權益
為切實防范化解新業態領域重大風險隱患,強化外賣送餐員權益保障工作,淮北市市場監管局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全力維護外賣送餐員合法權益。淮北

湖南漣源開展專項行動一對一為企業紓
位于漣源市的湖南三合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兩條生產線滿負荷運行,生產聚氨酯和巖棉復合板。因產品升級與產能擴充,急需新增兩條生產線,

湖南藍山縣進村入戶排查整治自建房安
老叔,這棟房屋墻體有開裂痕跡,要維修加固,安全重要!5月20日,藍山縣塔峰鎮果木村,黨員干部上門開展農村自建房安全隱患排查整治。連日來

一季度湖南萬元產值綜合能耗同比下降
近日,湖南省工業通信業節能監察中心發布一季度全省六大高耗能行業能源消耗統計監測報告。據該報告,一季度全省146家主要高耗能企業的萬元

濟南起步區一年來累計簽約優質項目11
萬里黃河第一隧濟南黃河濟濼路隧道建成通車,占地4000余畝的新能源乘用車零部件產業園加快施工……記者21日采訪獲悉,建設實施方案獲批復一

山東發布通知啟動傳統民居保護利用試
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省財政廳近日聯合印發《關于做好傳統民居保護利用試點工作的通知》,在全省部署開展傳統民居保護利用試點工作。此次試點














